又或者你對歌曲或樂團沒興趣,看完這個落落長的故事若能激起一絲「啊不然聽跨麥」,按下play鍵的衝動,那我會非常開心,每天含笑光泉(牛奶)。
為了戒掉愛拖延的惰性,Musitale以後固定每週三登場,如果沒人看.......,我會把它全部默背下來當我未來小孩的床邊故事,每晚固定放送到他耳邊,然後......,等他長大,我會送他去看心理醫師的。

2010
相隨百步 也有個徘徊意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這句用來安慰失婚的友人是再好用不過了,用於嘲笑那些老是說話不算話,說要復合,卻一直在外面找野女人野男人亂來,搞一堆私生子side projects的那些樂團是真的很好用,讓我們年復一年癡癡望春風,至少傷心欲絕時不用拿心愛的唱片黏在機車後輪當反光鏡,自我安慰一下也是百無一害。但今年可說是樂壇吃回頭草風氣最盛的一年,從年初的Blur,Pixies,The smashing pumpkins,Plup。這些說謊成性的老妖精竟然扯得下(對方的)老臉乖乖扮演親戚不計較的大和解戲碼。複合之團何奇多,騙錢騙我們感情,不乖乖進錄音室錄新歌只顧著用懷舊金曲巡迴撈金的也是不計其數。俗話說當你把信用卡刷爆的時候就是跟前男(女)友復合之日,把這個公式套進昔日走紅樂團,當你已經無法支付前妻巨額贍養費的時候,就是你向前團員們釋放善意的最佳時機。
九五年portishead一鳴驚人,一曲〈glory box〉沒人想到這種林投姐招魂的樂風也可以成功銷售經典牛仔褲。跑去演第五元素後又脫隊Massive attack的Tricky也接著與路邊搭訕的未成年少女Martina錄了唱片。Trip hop 三巨頭儼然成型,Bristol從一個相對其他發光發熱的鄰近城市來得邊陲的小鎮躍身一變成了英國的酆都。倫敦三人團體Morcheeba由Paul Godfrey、Ross Godfrey兄弟檔和黑人女主唱Skye Edwards組成,在一片trip hop榮景下也算是穩紮穩打,風格雖然變化頗大,但團員之間的摩合卻在第四張專輯《Charango》才出現變化。人雖然是習慣的動物,但是也是習慣將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的動物,後知後覺的Skye在兄弟倆半推半就下被逼宮走人。然後就和上述講的理由那樣,不管是缺錢還是缺愛,Morcheeba又重回對方懷抱,復合情節情深深雨濛濛,Skye與Ross在倫敦大街上巧遇,開啟了再續前緣的契機。老戰友合作的默契在樂團的第七張專輯《Blood Like Lemonade》雖看出明顯吉他導向的特色,但是電味有餘,只可惜那個年代氛圍不對,整張專輯聽下來讓人印象深刻倒還真無法細數,最喜歡的一曲《Blood Like Lemonade》也是專輯名稱,反而是法國le cargo團隊錄製下的不插電版本最為動人(最悲劇的一點是專輯並未收錄這個版本)。那種歷經滄桑又帶著淡淡恨意的感覺由這般歷經改朝換代風波的Skye唱起,實在讓人不寒而慄。就像友人喜愛的那句話:「相隨百步 也有個徘徊意。」割捨不掉,那就三思後再動手吧,砍掉可以重練,心碎可以黏回去。但是,熱情也可能隨著船過水無痕,再也激不起樂迷的漣漪了。
時尚、風水輪流轉,那麼樂壇20年一個輪迴也應該是這麼回事。前世與你撕破臉,叫你回家找媽媽的前團員們,現在卻對著媒體真心喊話叫你回家拾起樂器,企圖說服你們朋友還是老的好,這番銀貨兩訖的誠意,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欣然接受的(Ian Brown你到底聽到了沒?)。
Musitale:Blood Like Lemonade
她蹬著腳跟,一個腳錐子接著一個腳錐子躍過地面大小不一的水窪,懷著忐忑的心情在小巷雀步著。現在的確不是踩高跟鞋的恰當時機,她有點懊悔撇了撇嘴角,腳步卻不曾停緩。
兩棟建築物之間交疊闢出的那條小危巷,明顯是都市更新和炒地皮的那群狗人兩敗俱傷後留給城市的一道疤。她腳下黑色踝靴的纖細鞋跟左右劃開,像進行某種節奏割開這條疤,她忍不住幻想等等見到那兩個男人的場面,下意識摸了摸鼻端和額前是否出油得厲害,而臉上的殘妝是否還有宣示作用。七年前還是學生的她,在油膩膩的中餐廳端了三個月盤子,存夠機票錢,才得以飛到地球另一面,一塊沒有落日的國度與他們見面。熬了一整段有錢富婆肌膚烤地漂亮的古銅夏日,伺候那些拿筷子跟射飛鏢一樣驚險姿勢的老外,替他們奉上難吃的中國食物。一道道紅艷,濃稠化不開的血痰鋪灑在各式炸過的過期肉塊上,他們吃的很樂,有時這般拼貼的「糖醋」味道還不夠稱胃,他們總是吆喝再來點番茄醬。
「一群沒進化的野人。」在廚房窗口、桌椅和滿室人煙打轉的她,就不停在心中咒罵這群沒有美食味蕾的蠢蛋,以度過漫長夜晚。販賣勞力的疲乏時程幾乎銳利地要穿透那時的她。可是沒有,她走了過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
轉了彎出街,路上行人擁擠,臉孔卻模糊不清。她加快腳步,疾步行走。「希望不要遲到啊!」原本緊繃的雙拳,食指疊上中指,她默默祈禱著。
第一次與他們相遇是在鬧市裡一間位於二樓舊公寓,不起眼的二手唱片行。那天是假日,朋友們都驅車鑽過腸子般的山腰腹,到盆地的另一邊游泳,那片綠色的海每到假日就充斥著數量驚人,穿著暴露的異鄉客。晚上她得打工,哪裡也逃不了。時間剩一點點可以浪費,一個有門禁的摩登孤魂遊盪在燈火闌珊的夜晚,可是找不到伴陪著消耗。
她隨意翻著入口處一疊新進的唱片,雖說是新貨,在二手店也只是被遺棄的證據。手指像是可以閱讀文字那般,滑過每張樂手和專輯名目,最後在「莫奇巴Morcheeba」這個非常亂來的中譯名上駐留了那麼一刻,她展現極高的疊疊樂技巧把那張唱片拿出來,卻忍不住心裡低級的笑意無限擴大,在心裡默念了幾次諧音終於忍不住顫動的肩膀,像投石的水紋越擴越大。專輯還留著封套,是今年暑假的剛發行的專輯,根本不應當出現在此種場合。有本她始終提不起勁看完的法國小說提過:「幸福的故事聽起來都差不多,不幸的故事卻不逕相同」,年輕女孩子墮入風塵看了讓人嘆息,這張土耳其藍和磚紅色塊拼貼的嶄新專輯不知在怎樣無奈情況下被哪個急需變現的收藏家出賣。
兩位黑人和白人男性有說有笑在結帳櫃檯前用流利的國語跟老闆殺價,他們看起來就是這一區再尋常不過的國際學生,音量總是不自覺提高,顯得過度激昂,不知道到底開心什麼勁。讓人看了就有氣。她努力耐著性子,腳板卻忍不住打起趕人的拍子。黑人男性察覺到背後傳來的刺意,轉過身朝她露了一排刺眼的笑。他上道點點白人的肩示意,迅速結完帳。她則扯了一個眼神飄移的應付笑臉表達一點基本進退禮儀。
出了唱片行,那兩人蹲在樓梯口抽菸瞎聊,一來一往重音頓挫的英語在看到她下樓便嘎然止住,「不豪衣思,窩們港港不是故意的,客以原諒窩們嗎?」他們用音調控制得不太精準的國語示出善意。
閒聊中得知他們來自倫敦,高中畢業後從家鄉Bristol搬到東倫敦跑趴度日,每份工作從沒超過半年,常常下午睡醒確定當天晚上支持的球隊沒有比賽,就拽著一整個背包的唱片往地下舞廳跑。如果讓他們遇到「在人生的藍圖中,五年後你覺得自己應該變成什麼樣子」這類的尖銳的面試問題,大概會回應「啊,依生活方式推論,客觀來說應該是又禿又胖吧,即使這樣,很多比我們更難以入目的人類還是繼續在這世界爬行。五年也好、五十年也好,只要活著,對於變成什麼模樣耿耿於懷的,應該是小心翼翼這題答案正確與否的人。他們擔心完了才會輪到我們吧!」有時喝了啤酒,酒客也醉意充腦的時候,舞廳老闆會讓他們兩人上DJ台胡搞一場。窮酸的兩人長年窩在窗外風景很糟糕的擁擠破公寓裡,攀繞而上的樓梯轉角隨處可見尿漬的蹤影,二手傢具被撿回來的野貓嘶嚙地垂垂老矣,有時白天陽光照進屋子裡,貓毛、塵璊、懸浮粒子、菸灰在半空中昇華,強光折射下無所遁形,「just like heaven」他們兩個異口同聲唱出那幕風景,白人手在大腿上打拍子,幫朋友接話哼起了歌「Soft and lonely, lost and lonely……」(註1)。偶然一次機會下聽朋友說起來這裡教英文好像很好賺、啤酒又便宜,ㄧ次賽馬僥倖押對寶,衝動之下花掉所有積蓄買了單程機票從一個冷傲的島國到另一個熱切的島國換個時區鬼混。他們喜歡在酒酣耳熱之際放些沉重的電子樂。「讓人心情低落的電子樂」,他們倆是這麼默契十足地向她描述喜愛的樂風,對比他們臉上的那掛不正經,這番形容真是直接的可愛。她說Martina的聲音讓她沉迷,是柔軟的磁鐵緊緊吸住Tricky的鬼魅,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與之同行,就算轉角跌落地獄(註2)也不心慌。他們聽完笑了,問她:「那你知道Martina怎麼被Tricky挖掘的嗎?」
「Tricky有天在路上發現一個坐在牆邊哈菸的15歲女生,就是Martina,看她穿著制服一副不良的樣子,跑過去搭訕,結果後來……,」
「唱片做出來,孩子也有了。很難相信這樣酷到骨頭裡的音樂製造起源居然聽起來這麼像二流的搭訕戲碼吧!哈!哈!哈!」在一旁的Godfrey興奮地搶著接話。
另一個Godfrey也笑了,不過很快歛起笑容「不過這些都是我們小時候的事了,長大後搬到倫敦,現在又來到這裡。一開始對抗嘻哈入侵的trip hop,幾個巨頭還在,可是屬於Bristol的黑暗勢力卻早已消散地不知去向?」
是的,他們倆人都叫Godfrey,並宣稱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雙胞胎。她不相信他們的鬼話。一點也不。可是找到同我族類的好感卻燒的莫名旺盛,塞到最角落的位置維護那點火花。
後來的發展是更老套的搭訕故事了。三個年輕人蒸騰了一整個城市的夏日蜃樓。她搬進他們頂樓加蓋,亂巷叢生的灰色公寓,那樣的住所屬於熱帶盆地裡所有新貧青年的屬地。整個窗戶望出去大大的屋頂是他們的遊樂場,白天他們躺著曬太陽,抓天上飛機吃,許了些什麼願望?她現在回想起,遺忘也好。年輕時亂許下的承諾都是一個手指的力道就能傾毀夢想的那種願望。
整片醜陋、參差不齊的天際線也是他們三個人的,雖然要是認真談論,比起倫敦或是Bristol其實是更掩面不堪的程度。他們勾肩、搭背、胡鬧、一起用狠勁十足的台語髒話教訓在酒館亂搭訕她的其他老外,還有淩晨一點不切的雞排和梅子可樂串起這邊總算有一樣不亞於英國的垃圾食物回憶。他們流連那間像城堡一樣神秘的古董店,裡頭年代久遠,待價而沽的珍品隨著他們一時玩鬧的劇場換幕、退幕,三人接力扮演一個又一個憤世忌俗的失敗青年。在吵雜的街道上很沒公德心地並肩漫步。他們也曾大半夜偷偷溜進違建山寨把兩位Godfrey混音的卡帶一一投遞在入口前,像老兵報數那樣擠在一隊的綠皮信箱,期待引起某位繭居藝術家的興趣,後來當然沒有。他們只是那個時代戀棧肉身不肯放手的幽魂,有了同伴相互取暖罷了。
在行走中,有個小孩突然誤認了媽媽,拉錯了她的手,她愣地在逆向的人潮中定住了一會兒,全身制止不住拔腿狂奔,熟練從一家店舖的後門穿過一排及膝的雜草,拉起裙襬,跨過一個一米高的小丘,眼前已完全遠離市郊,只剩夜晚的草露搔著她的腿。
有時她鑽進他的床,有時另一個他溜進她的卡通內褲裡,有時她會獨自在房間醒來。
後來的某天,他們真的不見了,徹底蒸發。那些行走的遺跡還留著,可是他們離開了。皺巴巴的空煙盒還在,菸霧消散了。嗅覺還依賴過去,可是看去的那方空寂卻無法自欺欺人。季節走到下一季,他們三人卻不復同行。飛機依舊每天從陽台騰過,只是沒人用手抓來吃。
她在小丘的頂端終於歇下腳步,由這個角度望去底下一片漆黑。她脫下跟鞋,揉了揉腳跟,回想起那封飄洋過海的信。告訴她不告而別的理由,是他們其中一人隱藏不住那不光彩的疾病,怕她承受不住打擊和隨之即來的信任瓦解,便連夜倉皇逃走。她默默發了瘋,沒有人知道。每天拿鹽巴搓自己的身體,洗去不潔,一切徵兆未明,她採了幾滴血混在貓罐頭,在半夜誘惑飢餓的貓群,豢養黑洞那般要吞噬自己的恨意。後來,貓咪們也不再親近她了,鄰居也是。夜晚很安靜,時間溶蠟般滾燙,刻蝕滿地的滴滴答答。枯槁不成人形的她,決心帶著在中餐廳打工苦心攢下來的積蓄,買了前往倫敦的機票,並搬出那棟公寓。
她在倫敦準備了好久的驚喜,打算親自送給他們。在街上流浪,乞討,喝醉了攤在路邊,扯開嗓子賣唱,孑然一身在異地重現三個人的精選片段。有天,她的願望終於成真。在倫敦Paddington車站,那個匆匆上車的身影,她一眼就認出,滿心竊喜跟上腳步,躲在後節車廂。一部電影的時間結束(註3),她尾隨著他下車,Godfrey見到她,臉上那抹驚訝的表情瞬間隱沒。同情她一臉破爛,Godfrey忍不住舊情,客氣地請她回到住處梳洗。
「Godfrey也在啊,不過現在狀況不太好,唉,我跟你提過的,像信上講的那樣。」
他們兩個都沒有分開過,一直以來都是這樣不離不棄的。她想起初次見面時,他們說是雙胞胎的這回事,就覺得被幽了好大的一默。一個海地出生的黑人,和一個希望每天都是聖誕節的猶太人,他們是雙胞胎。
在Godfrey拿出鑰匙開門那剎那,她很適時地給了他們驚喜,不多也不少,剛好兩人份,一失神就灑了滿地紅艷。
「那些以前吃的飛機總算沒白吃。」她掀起裙襬拭乾淨門把上的指紋,然後下樓,關於他們初識時買的那張唱片和飄零迷魅一整個十年的樂種,孕育於此的土地,她一刻也沒多停留。
從最後的片段醒來,她走到一片灰色高低岩塊錯落的墓園,在兩塊題著「we drank blood like lemonade」的石碑上,她將手上的跟鞋扔到一旁,手枕在腦後,跟他們用相同姿勢一起躺著看夜晚黑的好似沒有邊界的天空發呆。終於,他們三人隔了七年再度交會。
他們已不在,黑色的血還在她體內汩汩流瀉著。
--------------------------------
註1> 英國樂團 The cure 一曲的歌詞
註2>
註3> 從倫敦搭火車至Bristol車程約90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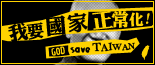


2 則留言:
amazing.
謝謝,這樣以後我亂寫就更有動力。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