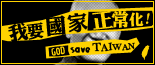2012年6月25日 星期一
大逃殺
如果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開玩笑,那就沒有任何事情能嚴重到傷害身心的吧。
世界當然不是這樣運作的啊,不然人生怎麼分辨輸贏呢?怎麼解釋看著對手癱軟在地上,自己內心升起的那撮小小快感呢?
我看著滿地的髮,想著裏面藏著怎樣骯髒的故事和讓我無處可躲的羞辱,然後不自覺開了幾個玩笑,就草草結束儀式。
當慣用焦慮面對酒精的夜晚蛻去上一季的軀殼後,隔天太陽升起,我逼自己騎著歪斜的單車開起歪斜的一日,我以為我還能一樣的平靜,可以平靜地用卡通的口吻說著自己如何用肉身撞碎鏡子、如何吐了一地又一地、如何抵抗六個大男人的力氣從救護車奪回房門口。
然後,我明白,只有一件事我始終無法輕鬆面對。因為太真實了,真實到我大概十萬年前就逼自己要忽略的東西。那一晚有很多畫面都是片斷的,我也無從記起連續的映像,我跟他們都說那晚其實沒什麼記憶了,但當我哭喊著你的名字,吼叫質問著空氣或是幻想中的你,知不知道我被欺負時,我其實是清醒的不得了。清醒到我能清楚感受到那憤怒和絕望有如刀割臉頰,一刀又一刀隨著眼淚、哭喊和鼻涕一再摧毀補補縫縫的精神狀態;清醒到我一輩子都不想在外人跟自己面前看到這模樣;清醒到我知道這必須是此生最後一次這樣神風特攻隊的崩解;清醒到我一輩子都無法用玩笑掩耳盜鈴。
伴隨而來是第一次失眠。三個小時,我聽著門外的對話,不間斷的聲音和熟悉的口吻捲著過去那些無形的嘲弄,有形的文字如何在深夜的裂縫茁壯為啃人不擦嘴的獸。我說我一直聽見聲音,但他似乎是沒搞懂,他說乖乖睡喔明天帶我去驅魔,也帶著過來人的高傲姿態對我說著這樣你就懂失眠的痛苦了吧哼哼。但這不是失眠,這是無法起身的惡夢。我內心對他說幹你娘,但我外在全都碎掉了,只能不斷掙扎著殘骸求一點平靜。把他當工具做了一場沒有愛的愛,我以為累了就可以好好睡,就像小時候煩惱不知所措的明天,而無法入睡時,就會故意把自己弄哭。生理上的疲累就是對自己最好的救贖了。套回內褲,我終於睡著了,做了一場失眠的夢。
寫得亂七八糟像大法師噴吐,如有雷同,必屬虛構。
訂閱:
文章 (Atom)